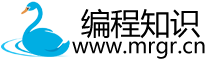初探哲学世界
文章目录
- 哲学概念
- 哲学分支
- 哲学价值
- 哲学经典
- 经典著作简介
- 《科学革命的结构》 - 托马斯·库恩(1962年)
- 《科学革命的结构》简介
- 《科学革命的结构》序言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同探讨一个古老而又充满魅力的学科——哲学。哲学是一门探讨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和语言等基本问题的学科。它涉及对世界本质、人类生活意义和道德行为准则的深入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哲学概念
哲学的核心在于通过理性思考来理解世界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它不仅仅是一门学术研究,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法。哲学家们试图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哲学分支
哲学可以分为多个分支,每个分支都专注于不同的问题和领域。
-
形而上学
- 探讨存在的本质、宇宙的根本结构以及现实的根本性质。这包括对时间、空间、因果关系、自由意志和物体本质的研究。
-
认识论
- 研究知识的本质、起源、范围和限制。它探讨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以及认识过程中的真理、信念、证据和理性的作用。
-
伦理学
- 专注于道德行为的原则和理论。它研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及如何判断行为的道德性。伦理学探讨善与恶、正义与不公正,以及个人和社会应该如何行动。
-
美学
- 研究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和功能,以及审美体验。它涉及对美、丑、品味、风格和创造性表达的分析和解释。
-
逻辑学
- 研究有效推理的原则和形式。它涉及对论证和推理过程的分析,旨在区分有效的推理与无效的推理。
-
政治哲学
- 探讨政府、正义、法律、权力、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利等概念。政治哲学试图理解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政治制度的理想形式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
宗教哲学
- 探讨宗教信仰、神的存在、宗教经验的本质以及宗教与理性、道德和科学之间的关系。
-
历史哲学
- 探讨历史的本质、发展模式和人类历史活动的意义。这包括对历史进程的解释、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时间的本质、历史变迁中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辩论,以及历史对个体和社会身份的影响。
-
军事哲学
- 研究战争、军事行为和国防的哲学分支,探讨战争的本质、目的、合理性和道德问题。
哲学价值
哲学的价值在于追求智慧、深化对世界和人类存在本质的理解。它通过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分析,探索知识、道德、意识、语言和现实的基本问题。哲学提供了评估生活意义、指导行为和决策的框架,促进个人和社会的理性发展。
哲学经典
哲学史上有许多重要的著作,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古典时代
- 《理想国》 - 柏拉图(约公元前380年)
- 《尼各马科伦理学》 - 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30年)
-
中世纪
- 《神学大全》 - 托马斯·阿奎那(1265-1274年)
- 《论君主的教理》 -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513年)
-
文艺复兴时期
- 《论人的尊严》 - 埃内亚斯·西尔维乌斯·皮科(1486年)
- 《君主论》 -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513年)
- 《方法论》 - 勒内·笛卡尔(1637年)
-
近代早期
- 《第一哲学沉思》 - 笛卡尔(1641年)
- 《利维坦》 - 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
- 《人类理解论》 - 约翰·洛克(1690年)
-
启蒙时代
- 《哲学通信》 - 伏尔泰(1733年)
- 《自然宗教对话》 - 休谟(1779年)
- 《社会契约论》 - 卢梭(1762年)
- 《纯粹理性批判》 - 康德(1781年)
-
19世纪
- 《精神现象学》 - 黑格尔(1807年)
-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 叔本华(1818年)
- 《共产党宣言》 -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
-
20世纪
- 《存在与时间》 - 海德格尔(1927年)
- 《科学革命的结构》 - 托马斯·库恩(1962年)
- 《哲学研究》 - 维特根斯坦(1953年)
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教会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质疑、如何寻找答案。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工具,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指导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找到方向。
经典著作简介
《科学革命的结构》 - 托马斯·库恩(1962年)

《科学革命的结构》简介
-
《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在书中提出了“科学范式”(paradigm)的概念,认为科学发展不是线性累积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科学革命”来实现的。在这些革命中,旧的科学范式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从而改变了科学家对世界的看法和研究方法。
-
库恩将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和“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两个阶段。常规科学是在特定范式指导下的科学实践,科学家们在这个阶段解决的是范式框架内的问题。而当出现与现有范式不符的“异常”(anomalies)时,可能会引发危机,最终导致科学革命,从而产生新的范式。
-
库恩的这些观点挑战了传统的科学发展观,即科学是不断积累和逐步接近客观真理的过程。相反,他认为科学进步是通过一系列不连续的、颠覆性的变革来实现的。这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也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
《科学革命的结构》序言
本书是大约15年前构想的一项计划的第一份完整出版的报告。那时我还是读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生,即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有幸参与了一项实验性的大学课程,为非理科生介绍物理学,从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令我完全始料未及的是,对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了解,彻底颠覆了我关于科学本质和科学之所以特别成功的理由的一些基本观念。
那些观念部分来自我以前所受的科学训练,部分来自长期以来我对科学哲学的业余兴趣。不知怎的,无论这些观念在教学上有何用处,在抽象层面似乎有多么合理,它们都与历史研究所呈现的科学事业完全不符。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对许多科学讨论都十分基本,因此它们的失真似乎值得彻底研究。结果,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剧变,从物理学转向了科学史,然后又从相对直接的历史问题逐渐转回到最初把我引向历史的更为哲学的问题。除几篇论文外,本书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以这些早期兴趣为主导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试图向自己和朋友们解释我当初是如何从科学转向科学史的。
哈佛大学学者会(Society of Fellows of Harvard University)提供的三年“青年研究员”(Junior Fellow)奖学金,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深入探讨本书的某些观点。如果没有那段自由的时光,转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会困难得多,甚至可能失败。在那些年里,我把部分时间花在了科学史上。特别是,我继续研究了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著作,并且初次接触到埃米尔·梅耶松(Emile Meyerson)、埃莱娜·梅斯热(Hélène Metzger)和安内莉泽·迈尔(Anneliese Maier)的著作。他们比大多数其他现代学者更清楚地表明,在一个科学思想准则与今天流行的准则大不相同的时期,科学思考是什么样子。虽然我对他们某些特定的历史诠释逐渐产生了质疑,但他们的著作连同拉夫乔伊(A. O. Lovejoy)的《存在的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对于形成我的科学思想史观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原始资料。
然而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探索其他领域,这些领域与科学史并无明显关联,但研究它们所揭示的问题却类似于(xli)科学史让我注意到的问题。一个偶然看到的脚注使我注意到了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皮亚杰阐明了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各种世界,以及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过程。一位同事让我去读知觉心理学的论文,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著作;另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了沃尔夫(B. L. Whorf)关于语言影响世界观的各种推测;蒯因(W. V. O. Quine)则使我理解了分析-综合区分这个哲学难题。这种自由的探索正是哈佛大学学者会所允许的,也只有通过这种探索,我才会碰上卢德维科·弗莱克(Ludwik Fleck)那部几乎不为人知的论著——《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Basel,1935),它预见到了我本人的许多思想。弗莱克的工作连同另一位年轻学者弗朗西斯·萨顿(Francis X.Sutton)的评论使我认识到,那些思想也许需要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中才能确立。虽然接下来我很少会引用这些著作和交谈,但它们对我的帮助超出了我现在所能重构或评价的程度。
在身为青年研究员的最后一年,波士顿的洛厄尔学院(Lowell Institute)邀我讲演,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试验我尚不成熟的科学观念。于是1951年3月,我一连作了八场公开讲演,题目是《追寻物理理论》(The Quest for Physical Theory)。第二年,我开始正式讲授科学史,此后将近十年,由于是在一个我从未系统研究过的领域教书,我很少有时间将最初吸引我进入科学史的那些观念阐述清楚。不过幸运的是,那些观念为我的许多进阶课提供了潜在的方向和某种问题结构。因此,我要感谢学生们给予我的宝贵教训,使我的观点更加可行,也使我的技巧更适合有效地表达它们。我在青年研究员期满后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历史研究,而且主题多样,上述问题和方向使其中大多数研究获得了统一性。其中一些论文讨论了某种形而上学在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些论文考察了相信一种不相容的旧理论的人们是如何积累和吸纳新理论的实验基础的。在此过程中,它们描述了我在本书中所说的那种发展类型,即新理论或新发现的“出现”(emergence)。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联系。
孕育本书的最后一个阶段始于我应邀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Advanced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度过的1958—1959年。我再次能够全神贯注地思考以下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共同体中度过一年,使我面对着一些出乎预料的问题,涉及这些共同体与我接受训练的自然科学家共同体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关于什么才是合理的科学问题和方法,社会科学家之间的明显分歧在数量和程度上都令我惊讶。历史和亲知都使我怀疑,对于这些问题,自然科学家的回答是否比社会科学家的更为可靠或持久。然而不知怎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实践通常不会引出关于基本问题的争论,而在今天的(比如说)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当中,这些争论似乎已经司空见惯。试图发现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我后来所谓的“范式”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我所谓的“范式”是指一些得到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为某个研究者共同体提供了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一旦看清楚我的疑难的这个部分,本书初稿便很快成形了。
这份初稿的后续历史在此不必赘述,但关于它几经修改所保留的形式需要交代几句。直到第一版完成并作了大幅修订,我都以为它会作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的一卷问世,这是一套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编辑们先是向我邀稿,然后坚定地让我作出承诺,最后又以无比的通达和耐心等待结果。我非常感激他们,尤其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对我的鞭策以及对文稿提出的建议。但由于《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篇幅有限,我只能以极为简要和提纲挈领的方式表达我的观点。虽然后来发生的事情使这些限制有所放松,并使该书有可能同时单独出版,但它仍然是一篇论文,而不是我的主题最终需要的完整的书。
由于我最基本的目标是敦促学界改变对我们所熟知的资料的看法和评价,所以初次表达时采取纲要形式并不必然是缺陷。恰恰相反,有些读者因自己的研究而认同这里所倡导的重新定向,也许会觉得这种论文形式更有启发性和更容易理解。但它也有不利的地方,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应当说明,我希望最后能在一本篇幅更大的书中就广度和深度进行扩展。历史证据要比我下面所能探讨的内容多得多,而且证据不仅来自物理学史,也来自生物学史。我决定只讨论物理学史,这既是为了增加本书的连贯性,也是基于笔者目前的能力。此外,这里提出的科学观为历史学和社会学中一些新的研究类型指出了潜在的用途。例如,反常或违反预期以何种方式吸引了科学共同体越来越多的注意,就需要做详细研究。消除反常的努力一再失败,从而引发危机,也需要做这样的研究。再如,倘若我说的不错,即每一次科学革命都会使经历革命的共同体改变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会影响革命之后教科书和研究报告的结构。研究报告脚注中所引技术文献分布的变化就是这样一种影响,它应作为革命发生的一个可能指标而加以研究。
由于内容被大大压缩,我也不得不放弃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例如,我对科学发展中前范式时期与后范式时期的区分显得太过示意和简略。在前范式时期竞争的每个学派都受到某种很像范式的东西的指导,在后范式时期也有两种范式能够和平共处的情况,尽管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仅仅拥有一种范式并不足以引发第二章所讨论的发展转变。更重要的是,除了偶尔的简要旁白,我并未谈及技术进步或外在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状况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然而,只要看看哥白尼和历法就会发现,外在条件也许有助于把一个单纯的反常变成一场重大危机的导火索。这个例子也表明,对于试图通过提出某种革命性变革来结束一场危机的人来说,科学以外的条件可能会影响他可选择的范围。我认为,明确考虑诸如此类的影响不会改变本书提出的主要论点,但肯定会为我们关于科学进步的理解增加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析维度。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篇幅的限制严重影响了我对本书历史取向的科学观的哲学含义的讨论。这些含义显然是存在的,我也试图指出并且用文献支持了其中主要的含义。但我通常不去详细讨论当代哲学家在相应议题上采取的各种立场。在我表示怀疑的地方,我更多是针对一种哲学态度,而不是它的任何一个明确表述。结果,一些知道并采取其中某种明确立场的人也许会认为我误解了他们的意思。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本书并不打算说服他们。若想说服他们,需要一本长得多又很不一样的书才行。
这篇序言开头的传记片段用以表达我对一些学术著作和机构的谢意,它们帮助我塑造了我的思想。对其他学人和著作的感谢,我将在以下各页的脚注中表达。但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以上所说和以下所述都不足以表达许多人对我的帮助,他们的建议和批评支持和引导过我的思想发展。本书的思想成形已久,若要列出对它有过影响的人,我的朋友和熟人几乎全都会上榜。因此,我只能列出少数几位最有影响的人,即使记性再差也不会想不起他们。
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柯南特最早引领我进入科学史,从而使我对科学进展本质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自那以后,他一直慷慨地提供自己的思想、批评和时间,包括阅读我的初稿,以及提出重要的修改建议。柯南特博士开设的那门历史取向课程,莱纳德·纳什(Leonard K. Nash)和我一起讲授了5年。在我的想法刚开始成形的那些年里,他是我更为积极的合作伙伴,在发展那些想法的后期阶段,我非常怀念他。不过幸好,我离开坎布里奇之后,纳什所扮演的知音等角色被我在伯克利的同事斯坦利·卡维尔所接替。卡维尔是一位主要关注伦理学和美学的哲学家。他所得出的结论居然与我的结论非常一致,这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此外,只有同他交流时,我才能用不完整的句子探索自己的想法。这种交流方式证明他非常理解我的想法,因此在我准备初稿时,能够指引我突破或绕过一些主要障碍。
初稿完成后,还有许多朋友帮我作了润色。如果这里只列出贡献最深远、最具决定性的四个人,我想其他朋友会原谅我的。他们是伯克利的保罗·费耶阿本德、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劳伦斯辐射实验室的皮埃尔·诺伊斯(H. Pierre Noyes),以及我的学生约翰·海尔布伦(John L. Heilbron)。在我准备最后的定稿时,海尔布伦常常协助我工作。我发现,他们所有的保留意见和建议都极有帮助,但我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或上面提到的其他人会完全赞同最后的定稿。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们,这当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谢。我可能最后一个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对我的工作贡献了思想要素。但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做了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让我继续做研究,甚至鼓励我为之全力以赴。任何曾与这样的计划苦斗的人都会认识到,完成它会让亲人付出多大代价。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
托马斯·库恩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62年2月